lol外围:达南客场击败斯特拉斯堡,夺得法甲胜利
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今天发布讣告称,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、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因病医治无效,于2017年5月7日7时21分在北京不幸去世,享年98岁。吴文俊是中国科大数学系的开创者之一。华罗庚、吴文俊与关肇直分别在科大数学系带一年级学生,史称“华龙”“吴龙”“关龙”。以下系中国科大口述校史访谈组记录的史实,以此缅怀。
大智为师:吴文俊先生访谈录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志辉 孙洪庆 王高峰 访问整理
摘要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,吴文俊先生到学校登台授业,至1964年因参加“四清运动”而离开讲台。访谈中,吴先生首先回忆起引导他走上数学学术道路的几位良师,之后讲述了他在中国科大任教时一些往事,最后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对当代数学教育的深远意义。
关键词 吴文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传统数学 当代数学教育
吴文俊教授在科大接受采访,2007年6月 丁星摄影
吴文俊先生(1919—),著名数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,在拓扑学、中国数学史、数学机械化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。吴先生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,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,1951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,1952年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,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(自然科学部分)一等奖;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今称院士)。
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(下文简称科大),为“两弹一星”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。根据“全院办校,所系结合”的方针,京区的一些研究所承担了13个系的创建和教学工作。其中,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担任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任,吴文俊先生到学校为58级力学与力学工程系的学生教授数学课程,之后他承担了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的教学工作。创办之初的科大数学教育采取“一条龙”的教学方法,即由华罗庚、关肇直和吴文俊分别负责一个年级的专业课程,他们被尊称为“华龙”、“关龙”、“吴龙”。吴院士全面负责该系60级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学生的数学教育,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。
1964年“四清运动”开始后,吴文俊被派到安徽省六安地区的农村搞“四清”。“四清”结束后吴院士回到北京,由于爆发了“文化大革命运动”,他被迫中断了在科大的教学工作。1969年冬,科大执行有关高校撤离北京的指示,下迁到安徽省合肥市,吴文俊失去了与学校的联系。“文革”之后,科大采取一系列创新发展的措施而名声鹊起。1978年吴文俊兼任数学系副主任。[①]自此以后,吴院士多次应邀来科大讲学,与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2007年6月5日,88岁高龄的吴先生再次应邀来到科大,为全校师生作了一场大型学术报告会,并与数学系的师生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和交流。吴院士在访问科大期间欣然接受了笔者的访谈,本文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,并经吴院士亲自校阅而成。
访谈时间:2007年6月5日上午
访谈地点: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家楼
一 早年学习和教学经历
问:吴院士您好,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。今天我们想与您谈一谈您和科大的情缘、您在科大工作的一些往事。首先让我们从您早年的学习和教学经历谈起。请您回忆一下,有哪几位老师对您走上数学研究道路有过重大的影响?
吴文俊(以下简称“吴”):关于对我一生数学研究有影响的老师,首先第一个是我初中二年级的几何老师。[②]因为当时发生了“一·二八”事变,我离开了学校,到乡下去。回来后一上课,几何都开始讲圆了。我前面的课程都没听,所以听不懂,干脆不听了,就看小说,结果到期终考试的时候就得了零分。暑假的时候,这位几何老师给我们补习。他很严格,经常要叫学生“吊黑板”,要你到黑板上,他出题目让你证明。我当时有许多错误,老师就指出来到底错在哪里。这样一来,我对几何上的认识、思考和方法就学到家了,那是关键的一个暑期。这个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,真遗憾啊,这是第一个使我走上数学道路的老师。
第二个老师是在高中一年级,有位老师也教几何。[③]他是福建人,讲话学生听不大懂,而且他讲得也不太好,所以不受学生的欢迎。可是这位几何老师,他在课外给了我许许多多难题让我做。经过这样的训练,几何的难题我做起来很熟练的,一来我就知道怎么做了。现在不行了,拿一道中学考试的题给我做,我做不来了(笑)。中学时候在数学方面对我有影响的,应该是这两位老师,都是几何方面的,让我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,而且有一些证题的能耐都在那时得到了训练。
到了大学,我想对我有影响的应该是大学一年级的老师胡敦复,他是系主任。[④]他讲课不慌不忙,但讲得非常清楚。一年级的微积分经过他讲授,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到了二年级,因为交大是工科学校,侧重于工科方面的应用数学,所以二年级我对数学没兴趣了,不想学数学。到了三年级情况就变了。三年级一位老师叫武崇林[⑤],他的一些课程讲得非常清楚,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态度。他讲的数学基础课程,对我非常有吸引力,还有高等代数、高等几何、群论、数论、微积分、实变函数论……受了他的教育以后,我就下了功夫,从此我就对数学产生了兴趣,特别是实变函数论。我受了课程的影响,从实变函数论走向点集拓扑,再后来走向组合拓扑(代数拓扑),这是决定性。武崇林使我从对数学不感兴趣变成非常有兴趣,而且他也特别地对我另眼相看。他经常借书给我,他家里藏书很多,都是从各个地方搜集到的,我记得有一本是印度出版的《代数几何》。我想这本书恐怕别的地方不会有,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,专门借给我看。我受他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,他经常借一些外面借不到的私人藏书给我看,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,我还经常到他家里去。
问:刚才谈到的武崇林老师对您非常关爱,那么是不是他已经发现了您在数学方面有非常好的天赋,能够培养成很好的人才?
吴:也有可能,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特别感兴趣。抗战时期,交大迁到内地去,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上海,他想要把我弄到交大去当助教,不过没成。抗战胜利以后,他一直就跟交大讲,要把我弄去当助教,也没成。在抗战时期没成,那么到抗战后也没成(笑)。这几位老师,初中的一位,高中的一位,还有大学的一位,这三个人对我的成长特别有影响,我非常感谢他们。
问:您大学毕业之后,在两所中学里当过教员,并且在上海临时大学当过教员。
吴:那是抗战时期,要谋生,家里面光靠我父亲养活不了家人,我也要找一些工作。当时班上的同学就帮我介绍到一个初中去讲一年级的代数。[⑥]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,第一个学校垮台了,后来介绍我到另外一个学校,[⑦]直到抗战胜利。每一个学校教的都是初中一、二年级,光是教书拿不到多少钱,所以我又兼一个教务员的工作。每天一早跑去点名,看学生自习课是不是到了,一个教务员要坐在那里,一天到晚直到下班。所以那个时候数学研究谈不上,没有时间。晚上也不行,因为家里住的很局促。我父亲也是一大早就要上班,晚上很早就要睡。那个时候都挤在一个屋子里,所以我晚上也睡的早,根本没时间。因此不但没有学习什么数学,而且把原来学的数学全部忘光了。
这是大学毕业以后抗战时期的几年,到后来日本人已经差不多快垮了。那个时候我在中学里面,当然没时间搞数学,可是相处很愉快,都是教师,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,大家很随便,什么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情形啦,都随便讲。后来才知道校长是地下党员,用办学校作掩护。他好像有意想把我吸引到这方面,所以借给我一些书。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《西行漫记》,许多共产党的知识是从这里了解的。后来他带我参加一些活动,他显然是想把我吸收到这个里面。但我不懂,觉得这个校长很好,就跟着他走。后来抗战胜利了,交大从重庆搬回来成立一家临时大学,有一个朋友帮助我当了这家临时大学的助教。[⑧]这样一来就有时间了,因为当助教不需要花多少时间,我可以重新复习已经忘掉的数学,这是很关键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影响,本来我跟中学的校长不是参加什么活动吗,就也不想干了。我又可以搞数学了,我马上就回到数学上面了。
问:那些时候您忘掉了很多数学,是因为各种复杂的生活困难?
吴:是的,现在可以搞了。我对数学的爱好,在交大经过武崇林的培养,已经扎下了根,只是因为客观条件,我没有办法,一有机会的话,我马上就回来了,重新搞数学。大概就是这样的。

问:您后来又留学法国,考的是中法留学交换生?
吴:是这样的。抗战胜利了,国民党政府回到南京了,教育部办了一个留学生的考试,其中有一项是跟法国政府建立中法交换生。法国派学生到中国来留学,他们学习的我想大概是中国的文学啊、历史啊,我不知道。中国到法国去的留学生,各行各业都有,文科、理科、法律教育什么的。一共好像招了40名中法交换生。我对这些东西都外行,教育部在报纸上登了,我也没注意.结果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,就是帮我到交大当助教的那个同学,他到我家里来就告诉我这件事,劝我去参加考试。临时大学有一位教授叫郑太朴[⑨],我给他当助教,他是不是地下党员我搞不清楚,反正是跟共产党关系不错。他突然跑到我家里,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家住在什么地方,也劝我去参加这个留学生考试。我本来不知道,后来两个人一劝说,我就去考了。因为我当助教当了一段时间,已经把忘了的东西都恢复了,所以我数学考试就没有问题了,其他语文、英语我不清楚,反正是通过考试了。数学一共四个名额,我考了第一,所以就到法国去留学了。
抗战结束以后,我的这个同学(赵孟养)想办法介绍我见到了陈省身[⑩]。陈省身在普林斯顿待了一段时间,在那里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,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数学家。他回来了以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。我那个同学通过特殊的关系介绍我去见陈先生,他就把我吸收到研究所里,当时叫做实习研究员,实际上是当他的研究生。他不仅是把我吸收进去,而且还请数学系出名的几所大学,每个学校送一个年轻有为的学生到他那里,一共大概有五六个研究生,跟陈先生学拓扑,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真正走上了研究道路。但是因为我考取了留法交换生,我见陈先生的时候还不知道,我考过就忘掉了。到第二年发表了,我考上了,教育部把这些考上的人弄到南京去,然后准备到法国,我就这样子离开陈先生。大概经历就是这样子。
问:您1951年回国后先到北京大学当了教授?。
吴:先到北京大学,教了一年,那时教得很糟糕(笑),教书跟研究是两回事情。
问:当时是教什么课?
吴:教微分几何。微分几何本来我就是外行,因为我在陈先生那里。在留学的时候学的是拓扑,没有学微分几何。那么就临时找一本书讲,讲得一塌糊涂。
问:是给数学系的学生教课?
吴:给数学系的学生。非常糟糕,很对不起那一班的学生。
问:但是我想,那一班的学生现在要回想起来,在大学期间能够聆听到您的讲课,应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。
吴:唉,就好像我在初中教课也是非常失败的。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教负负得正,我先这么教,后来发现不成。换一个教法,又不成。本来改了一下以为可以,到后来又不对头,学生就乱算一气了,反正是教负负得正,一直是失败的。这是在北京大学之前,抗战时期在中学教书的情况。本来我对中学老师很有感情的,对后来的中学校长也很有感情,我很乐意,可是我看我教书不行,这也是使得我决定回到数学研究而不走教学这条路的原因之一。
问:后来您就从北京大学调到中科院刚成立的数学研究所。
吴:这个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的事情了。
二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
问:1958年科大成立,当时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办一所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。科学院采取“全院办校、所系结合”的办学方针。您当时在数学研究所工作,是如何到科大工作的?
吴:我一点都不知道,突然临时通知我,成立科技大学了,你到科大去教课。我毫无思想准备。
问:是谁通知您的?
吴:当然是所里面通知的,具体是谁我忘记了。
问:当时数学所里的几位先生,像华罗庚、关肇直也都到科大去教课。
吴:我想他们都是事先知道,可是我不知道,是临时通知我去科大教书的。这个我对当时数学所的领导有意见,应该早点打个招呼,我对教微积分没什么经验,所以教得一塌糊涂(笑),应该早一些通知,至少有个思想准备。建立科技大学,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。我大概后来听说为什么要建立科技大学,因为科学院的年轻同志,都是由各个学校送来的,比如说北大,把毕业的一些好的同志,送到科学院来当实习研究员,各个学校都送一些。
可是后来发现,真正最好的人学校自己留下了,当然也不是把差的送来,也是好的,但不是最好的。科学院要解决年轻研究人才的来源,就自己创办一所大学直接培养,因为科学院有师资力量,虽然不一定教过书,可能没有经验,但能耐是有的。不管建立科技大学的动机怎样,这个做法是对的。对于研究人员来说,现在讲“教学相长”,当然要抽出一部分时间来从事教学工作,对于自己的研究也是有益处的,对我本人来讲,科大教书的几年,我受到很大的益处,意想不到的益处。
问:创办之初的科大数学系采取“一条龙”的教学方法,就是您和华罗庚、关肇直每位先生包一届学生。在科大校史上,建校之初的数学系有“华龙”、“关龙”和“吴龙”的说法,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吗?
吴:这个“一条龙”是人家叫出来的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反正不管什么样子,“华龙”是一条龙,“关龙”是一条龙,我根本称不上是“龙”。有一届由华罗庚包了,怎么教学、怎么安排教师,由他负责。我只是包了一届。

问:这是不是教学的一种改革,一种创新,一种新的模式?
吴:我不太清楚,反正人家这么叫。我也不能称为“龙”,反正有一班是我负责。
问:大概有多长时间,负责到他们毕业?
吴:一直到毕业。是这样的,先是普通的课程,一年级、二年级。到三年级呢,搞专门化,这由我提出来,建议建立几何拓扑专门化,不是专门拓扑,不是拓扑专门化,是几何拓扑专门化。在建立专门化的过程中,要吸收一些同学到班上来,一班有一百多人,有时候更多。当时有规定,专门化的人不能多,因为着重是应用、联系实际方面,不能都搞纯粹数学。所以人不多,大概十来个人,三年级、四年级,甚至再到五年级,我记不得了。反正我负责这个专门化,由我挑选几个人,也不是完全由我挑,你不能将好的学生都挑走了,可以挑几个好的,余下的由学校安排。
问:科大非常注重基础课的教学。
吴:是的,我从来都觉得这是科大相当成功的地方。而且,科大的学生,我的印象是不太搞政治活动,埋头在书堆里面,朴实认真。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,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全部精神放在教学上。
问:当时的学风如何?
吴:学风好,所谓学风好就是埋头学习。
问:那时您有没有发现几个非常喜爱数学的学生?
吴:有好几个。有一个我特别欣赏的,叫王启明,后来在美国出车祸去世了,否则的话他应该是中国当代数学界的学术领导。还有几个也可以,学术都很好,我有个名单,因为每年都要来祝贺我生日(笑)。我有他们的名单,而且记着他们现在干什么。
问:您是如何发现王启明对数学有特别兴趣的?
吴:当时可能是讲《高等微积分》,我不记得了,应该是在二年级。我是根据一个德国人写的教材来讲,因为我的德文比较在行。有一次,王启明跟我讲,说你讲的内容是不是根据那个德国人的,我想这个学生了不起啊,他懂德文。因为我没讲过,他知道我讲的内容是根据什么来的,我大吃一惊。还有一次,在讲课的时候,王启明说有一个地方讲错了,他指出来,我印象特别深刻。到后来专门化的时候,就把他吸引到班上来,讲几何拓扑。
问:您讲课自己编写教材吗?
吴:我当时讲课要有蓝本,不能自己编。华罗庚自己编了一套《微积分》来讲,关肇直也编一个教本,两个都印出来了。我没有教本,我讲课不成系统。他们有自己的看法,华罗庚和关肇直的教材都是不错的,也涉及到中国传统数学的某些内容,像无理数、小数等。华罗庚和关肇直不约而同,都是从这个地方入手的,讲小数,无穷小数可以代表任何实数,就从这里入手。先讲这个,相当于中国古代,然后再到比较现代的西方的内容。他们两种教本都是这个样子。
问:您当时是用他们的教材来给学生上课?
吴:我没有用他们的教材,当时也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教材。
问:当时课堂上课的场景是个什么样子?
吴:是一百多人的课堂。
问:您在科大工作的几年中,除了教学之外,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什么?
吴: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。反正那时候比较不稳定,一下子这样,一下子那样。在科大的五年倒是稳定的,一直教下去的,先教普通班,然后再办专门化。
问:您在1956年的时候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,那时候您非常年轻,37岁,第二年被增选为学部委员。在您的科研兴趣非常浓厚、并且处于前沿领域的时候,您到科大来搞教学工作,这种教学与科研之间有没有冲突呢?
吴:也可以说有一些,但关系不大。
问:您在教书的时候还是全力投入教学工作的?
吴:那个时候还是相当投入的。开头没思想准备,在力学系开课,教得很糟糕,后来教数学系,那时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有时讲得好,有时讲得不好,但是比较认真地教。
问:58年、59年的时候有一些政治运动,比如说在“大跃进”中,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,数学教学也要联系实际。当时数学系的教学情况是怎样的?
吴:开始没有思想准备,因为我是搞拓扑的,我想当时搞数学的也没想什么联系实际,没意识到这个问题,所以受到思想冲击,一下子接受不了。可是稳定下来再认真思考,“数学联系实际”提得对,数学应该联系实际,不联系实际的数学是错误的,这是我后来想的。这个对我的影响,基本是正面的,我接受了这个思想,这也影响到后来的一系列工作。开始我不理解,不能说抵触,就是不知道怎么做。那个时候搞得也不对头,跑到酱油厂去,还有跑到中关村的电话局,基本上是乱来一气,瞎搞,这个做法不对头。可是到后来,我确实接受了,联系实际就应该是真正地联系实际,这是对的。我现在变成数学联系实际的坚决拥护者,就是受这个思想影响,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的。
问:您是什么时间停止在科大上课的?
吴:到1965年,“四清运动”,班上的同学一起去的。那时候,我到了安徽六安。那个时候就离开了科大,等到“四清”回来,马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,天下大乱。
问:回来以后跟科大有没有什么联系?
吴:那个时候不可能有联系,文化大革命,什么事都谈不上。
问:后来科大就下迁了。
吴:唉,对啊,科大1970年就迁到合肥来了。
问:当时,您是如何知道科大要下迁的?
吴:科大下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,我知道,因为杨……,一下说不出来了。
问:是杨承宗?
吴:杨承宗!他来告诉我,因为杨承宗在法国的时候,我们已经有交往了,有时候也联系。他跟我说,科大要下迁到合肥,他也没说什么道理。
问:您从科大离开后,是否还在其他大学讲过课?
吴:没有。没这精力,也没这可能。
问:您曾多次来科大来讲学,应该说对科大有种特殊的感情。
吴: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家要找我,首先是严济慈,他当校长,老是要找我,而且要把我留在科大,我不干(笑)。我还是以研究为主,教育为次,兼职可以,要我撇开研究工作,这个我不干。严济慈是一定想要把我拉到科大来,科大要是在北京的话还可以考虑,在合肥就不可能了。恐怕他也想把华罗庚弄到科大,这个也不可能。
我也不喜欢行政工作,我对系主任,根本不……(笑)。我现在什么行政工作也不管,我从来都不管的,当所长、副所长的时候我都不管的(笑)。我不愿意当副所长,当就当了,结果走在路上一个年轻同志就找我,说他现在要房子,要我给他想办法。我说我不管这个事情,他说你不是副所长么?我说,这个副所长我也不想当,革掉最好了喽,本来我就不想当。真正当副所长,我还麻烦了,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都找上我了。我也不知道所长、副所长怎么当的,他们有这个本事,我没有这个本事。要我去分房子给他,我都不知道怎么弄。
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带名誉性质的,都是名义上的,我也搞不清楚,我接了很多名誉的,这个是名誉的,那个也是名誉的,我都不管。学术上的事情我管,不是学术上的我不管,我对社会活动也根本没兴趣。我只管学术方面的,比如说科大找我来做个报告,那我可以考虑,你要来一个什么名堂,那我……(笑)。
问:大家都对您的学识非常敬仰,您能推开这个行政方面的事情专心做研究,直到现在也是活跃在数学的前沿领域,也是大家非常敬仰的。
吴:我想应该是这样子。当然有人特别有能耐,可以又是做行政又做学术,我没这个能耐,我只好限于学术方面,行政我不敢过问。有能耐,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。
三 中国传统数学与当代数学教育
问:还有一个问题,您对中国传统数学非常喜爱,也非常有研究,您觉得中国当代的大学数学教育,是否可以引进一些中国古代传统的数学方法?
吴:应该是这样的。这要靠教师,教师自己对这个有认识,那么可以在课程里面适当地讲一些。靠外界促动是不行的。
问:您认为传统数学的方法对当代数学还是有一些启发和帮助的?
吴:我是走极端的啦。我不是讲过嘛,影响数学进展的决定因素是中国的传统数学,而不是西方的欧几里得数学。我那个时候说过,现在还是这个样子。当然,现在这个思想国内不接受,国外也不接受,我想慢慢会接受的,也有迹象表明现在是得到某种程度的认识。我去年得了邵逸夫数学奖[11],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,是为什么给我的问题。评审委员会是五个人,其中有一个中国人,北大的张恭庆[12],他当然支持我,但只有他一个人,可以想到他说话不会有太多力量。此外的四个人,主席叫阿提亚(M. F. Atiyah)[13],曾是英国皇家学会主席,获得过菲尔兹奖;一个是日本人,叫广中平佑(Hironaka)[14],他也得过菲尔兹奖;还有一个是俄罗斯人,叫诺维科夫(S. P. Novikov)[15],也是得过菲尔兹奖的,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格利菲斯(Phillip A. Griffiths)[16],他没得过菲尔兹奖,但他是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,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。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每年都要吸引很多年轻人到那里去,格利费斯对全世界数学的情况是了如指掌,而且他掌握数学的发展形势,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尽管他自己没得过菲尔兹奖,但他有许多很好的工作,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。这么几个人的评审委员会,评审结果是决定把这个邵逸夫奖给我和一个美国人,叫曼福德(David Mumford)。它的评语是这样的,因为我们走的方向是不约而同的,本来是纯粹数学搞出成绩,我是搞拓扑学的,曼福德也是搞纯粹数学的,后来两个人都转向计算机了。不同的原因,但都跑到计算机领域,而且在计算机应用到数学方面都做出了某种成绩。他们最后一个评语说,我们两个人的工作,代表了未来数学的一种发展倾向,大意是这样。这说明,我的那些做法,用计算机来从事数学研究,这是有道理的,它代表了将来的数学发展。我刚才说钱多少没关系,这个评语使得我非常高兴,说明我用计算机来搞纯粹数学,来搞数学,现在谈不上搞纯粹数学,是我应该继续下去的事情。
问:这种思想是从传统数学来的?
吴:是从传统数学来的。计算机科学有一个大人物叫克努特(Donald E. Knuth)[17],他说计算机科学说穿了就是算法的科学。中国的数学主要是算法,不是定理。什么定义、公理啦,中国根本没有,就是算法。按照克努特的意思,中国传统的数学是计算机的数学,因为中国传统的数学是算法的数学,我用计算机来搞数学,这是理所当然的了。邵逸夫奖说明了,国外也有一定的认识,至少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,有这个认识,我跟曼福德这个做法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我想慢慢会得到支持的。
问:您对传统数学是大力推崇的。
吴:我觉得中国传统数学的算法是适合计算机的,这方面一定能压倒西方,这是不成问题的。这是我个人的认识,对不对,现在没法说。当然,西方也有它可取的地方,需要动脑筋,就好像我在初中、高中的学习训练。可是这不是正路,我不赞成这个,早晚要被中国的数学淘汰。这是我的预言,将来考验是对还是错,也许我已经死了(笑),我自己不知道,后来的人可以知道。
问:那您感觉中国当代的大学数学教育,应该有什么样的做法?
吴:当然应该能够符合这样一个趋势。不过,这个主要要求教师要有认知,强加给教师,这个做法我想效果不会很好。中国有不少人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,国外也有这样的认识,我是去年获了奖才知道,跟计算机打交道的人当然对我有认识,这是自然的,但纯粹数学方面的人也有这个认识,这是我不敢想象的。这个是要慢慢来的,要有耐心,自然而然。
问:发扬传统数学的思想和方法,在当代大学数学教育中该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
吴:我想,在国内有不少人是认识到这一点的,也不是全部,反对的人也多得很,可是有不少人是支持我的。这是可以想象的。
问:您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数学的?
吴:对,完全是外来因素促成的。我本来不知道,也瞧不起中国的传统数学,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。后来是因为数学所的关肇直,他是我非常佩服的,他提出来大家学学古代数学。当时有一种复古倾向,关肇直提出学中国古代数学是比较合法的,因为拓扑你不能搞,一搞就要挨批的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大家也没什么别的可看,我也就这样,先看看究竟怎么回事,一看原来是这样子。这是要下功夫的,要跑图书馆、旧书店,也是花了一段时间,才慢慢理解的。什么事情都是这样,不是随便想一想,一下不劳而获的,哪有这么容易,都要下苦功。
问:您当时接触到中国传统数学,最早接触的是哪个领域?哪本著作?
吴:最早是看一些通俗的书,看古书看不懂的。我记得当时一个是看李俨,一个是钱宝琮。特别是钱宝琮的《中国数学史》,他用一些现代的话,将中国传统数学做一些介绍,这些可以看懂,究竟中国数学都讲一些什么东西。可是,光是这样是不行的,我知道讲了什么东西,根据这个必须再找原著,要找第一手材料。第一手材料刚开始看不懂,但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再来看第一手材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,怎么讲的。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,要下很大功夫。
结果在关键的地方,我发现了一个东西,就是中国古代量太阳的高,地面作为水平面,测量太阳离开地面的高度。这在很早以前,就有一个漂亮的公式,叫“日高公式”,还有“日高图”,这个图的来历要到公元前2世纪,秦朝以前,也不知道怎么来的,笼笼统统的一些话,看不懂了。三国时代吴国的赵爽,写了几篇相当于是现在的短篇论文,有一篇是“日高图说”,解释太阳的高度公式是怎么计算的。这个“日高图说”,它是有图的,画在绢上,上面还有五颜六色的,用颜色标注。当然这个图已经走样了,留下来的也是残缺不全的,还有个说明也几乎没法读懂了。就是利用这个走样的图,然后根据赵爽的“日高图说”,一步一步就可以把它证明出来。这是关键的一步,这么一来,我就决定下功夫了。这个是有道理的,中国的数学可以啊,究竟有多少东西,这个就说明了问题。这么漂亮的一个公式,而且有证明啊,赵爽的这个“日高图说”,我一句一句对照,把它得出来的。
中国人就喜欢跟着外国人跑。“日高图说”有这么一个日高公式,怎么来的呢?那么有人要证明,怎么证的呢?添一条平行线,这不是胡闹吗,中国哪来的平行线?中国历史上没有平行线的概念,怎么能随便画平行线呢?而且有的人甚至用tangent(正切函数)证出来,说这个公式是对的,tangent是哪个世纪才出现的?“日高公式”是在古代,公元前的秦汉初年的著作里出现的,哪里有tangent这个概念? 我曾提出几个原则,古代的数学应该以当时古代人掌握的知识来进行推演,不能用后来的东西。要有原则,不能乱来。这个“日高公式”得到成功,就说明中国古代数学有它自己的内容,这是我决定性的一步。此后,我就继续钻研,这就简单了,下功夫就行了。当然,我下功夫也不是都下在这方面,只是有一部分,因为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。我喜欢几何,几何问题看得比较多,还有一些其他的,因为我也不是搞数学史的,我是业余爱好吧(笑)。
问:您过谦了,我们先谈到这里,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!
吴:我乱说一气,想到哪,就说到哪。
参考文献
胡作玄、石赫 2002. 《吴文俊之路》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. 4-8.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78-WS-C-38. 关于聘请兼职系主任、系副主任请示报告.
作者简介:吴文俊,1919年生,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;张志辉,理学博士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;孙洪庆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生;王高峰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硕士生。
基金项目: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级重点项目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历史”。
[①]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78—WS—C—38。
[②]1931至1932年,吴文俊在上海民智中学读书。参见胡作玄、石赫 2002,页4-8。
[③]1933年,吴文俊在上海正始中学读高中。
[④]胡敦复(1886—1978),江苏无锡人,中国数学家、教育家。1909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,获理学学士学位。1928年获得美国荣誉博士学位。1930至1945年,胡敦复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。
[⑤]武崇林(1900—?),字孟群,安徽凤阳人。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,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。
[⑥]1940年吴文俊交大数学系毕业后,经人介绍到育英中学任教。
[⑦]1941年12月7日,“珍珠港”事件爆发,不久日军进入上海租界,许多学校停办。1942年夏,吴文俊到培真学校任教,并兼任教务员。校长叶克平为中共地下党员。
[⑧]1945年末,吴文俊到上海临时大学任郑太朴教授的助教。
[⑨]郑太朴(1901—1949),上海人,名松堂,字贤宗,号太朴。数学家、翻译家和革命家。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22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学。回国后先后于中山大学、同济大学、重庆交通大学任教,曾任同济大学数理系主任、教务长、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等职。
[⑩]陈省身(1911—2004),浙江嘉兴人,微分几何学大师。1936年获得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,1943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,1946年回国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并任代理所长。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,1961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,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。1984年获得沃尔夫奖,2004年获得邵逸夫奖。
[11]“邵逸夫奖”是由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人邵逸夫于2002年11月创立的国际性奖项。设有数学奖、天文学奖、生命科学与医学奖三个奖项,颁发给在数学、医学及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,其形式模仿诺贝尔奖。首届颁奖在2004年举行,邵逸夫数学奖 2004年颁发给陈省身,2005年为安德鲁?怀尔斯(Andrew John Wiles);2006年为吴文俊和大卫?曼福德(David Mumford)。
[12]张恭庆(1936—)上海人,北京大学教授,北京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,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199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,1996年至1999年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。
[13]阿提亚(M. F. Atiyah, 1924—),前英国皇家学会主席,三一学院院长,牛顿研究所所长,1966年获得菲尔兹奖。
[14]广中平佑(H. Hironaka, 1931—),日本数学家,1970年获得菲尔兹奖。
[15]诺维科夫(S. P. Novikov, 1938—),俄罗斯数学家,1970年获得菲尔兹奖。
[16]格利费斯(Phillip A. Griffiths, 1938—),美国数学家,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。
[17]克努特(Donald. E. Knuth, 1938—),中文名高德纳,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,是计算机算法和程序设计技术的先驱者。
吴文俊先生生平
吴文俊1919年5月12日出生于上海。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,1946年到中研院数学所工作。1947年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,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,随后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任研究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吴文俊于1951年回国,先后在北京大学,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,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任职。曾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、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、全国政协常委、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,中国科学院系统所名誉所长。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。吴文俊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开创者之一。
吴文俊对数学的主要领域—拓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“吴示性类”和“吴示嵌类”,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“吴公式”。他的工作是19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,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。1970年代后期,他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,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“吴方法”,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。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,他的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。
吴文俊曾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(2000)、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(1956)、首届求是杰出科学家奖(1994)、邵逸夫数学奖(2006)、国际自动推理最高奖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(1997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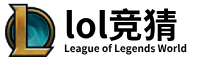
评论列表
发表评论